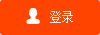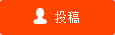互联网大厂狠抓贪腐:半年打车报销20万,前置仓成了煎饼摊-腾讯新闻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很多贪腐方式其实并不高明,要不要抓,怎么抓,都是“利益”的权衡
文 | 郑可书 刘以秦
编辑 | 刘以秦
王宣(化名)当警察七年,杀人、贩毒,五花八门的案子都查过,做过法医,解剖过尸体。能让他感到意外的事情不多,互联网公司贪腐案算一桩。
2019年,他加入一家社区团购公司做监察,负责查处贪腐、违规员工。他见证开城时的“烧钱”手笔:公司大量铺设前置仓,租一个仓库,至少要交半年房租,动辄几十万元,一平米但凡差一元钱,数额就大到“可怕”。
这家公司两位最低职级的员工,经手几十个仓库,通过谎报租金等方式,一年半的时间,合伙赚到200多万元。这让王宣意识到,在互联网行业,“职级非常低的人,反倒能赚很多钱”。后来,两人因职务侵占被判入狱。
从事监察工作八年的赵树远(化名),同样被互联网的富庶震惊。他在传统物流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都做过,对比发现,互联网公司比较年轻,风控制度不完善,且习惯用巨额补贴占领市场,涉案贪腐金额惊人——他经办的最大案子,公司损失了4000多万元。
过去十几年间,财富在互联网行业快速集聚。截至2022年底,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总市值已经超过10万亿元。在“新增长点”、“All in”、“迭代”的号角声中,滚滚的钱和资源顺着动辄万人规模的庞杂组织体系流向基层,腐败在此滋生。
这几年,降本增效成为主题,互联网公司格外关注每笔钱的流向。去年底,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一次内部大会上,称腾讯贪腐问题“触目惊心”,“看完之后吓死人”;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随后在内部直播中承认,“腾讯的那些问题,百度也都有”。今年1月,美团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称,2022年,美团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107人,并附上相关人员具体信息。这是美团第一次公开对外发布贪腐信息,此前仅在内网通报。
针对腐败的战斗打响了。大厂们设立监察、廉政部门,高薪聘请专业人员,动用数据等技术手段查处违规员工,“战果”通过内部邮件与网络分发,以示警醒。据南方都市报《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》,2021年,曝出舞弊案的互联网公司共22家,涉及案例超过240起,同比增长153%;超过300名员工被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,较前一年翻倍。2022年,数字再次增长:涉案公司37家,受罚员工超400名。
时代变了。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(化名)这样比喻:“以前,地主家的余粮很多,打小工的往包里揣一点,地主也不说什么;现在,地主家余粮少了,打小工的再往自己包里揣,就别怪地主不客气了。”
数据的权力
赵树远今年34岁,身高接近1米8,体重156公斤。这样的体格有利于他开展工作——搜集证据,揪出贪腐人员。
退伍后,他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一家传统物流企业当监察主管。这里还没有被信息技术改造,要想查案,他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,“靠自己两条腿跑”。
一年夏天,为了检查库位出租情况,他在冷库待两小时,一个个数。库外蒸腾的暑气,遇上库内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,在眼镜上结成霜。人工登记的财务数据显示,冷库位出租20个,但他计数的结果是25个。事后查明,多出的9万元租金,进了冷库负责人的口袋。
三年后,他来到一家电商公司工作,第一次感受到技术的力量。该公司将业务数据导入线上系统。之前需要他实地走访、翻看纸质文件查询的资料,如今在系统简单点选,就能获得。
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业务部门开发,并非专为监察设计。刚去的时候,赵树远连菜单名都搞不清楚,只能一个个向业务同事请教。在系统与数据的帮助下,他通过线上梳理获得线索,发现问题后再实地调查,原本每月20多天的出差时间明显减少了。
可系统是公平的,贪腐行为也被技术改造。赵树远的同行、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提到一起大闸蟹的案子。通常为促进销售,商家会花钱在电商平台投放广告,提高曝光率。但有的商家则选择贿赂平台人员,让他们在后台修改店铺展现率,然后等着流量和系统发挥作用——平台日活体量巨大,只需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,大闸蟹销量、店铺收入就能有明显提升。
另一位从业者提到抽奖活动:运营人员修改后台抽奖逻辑,调高特定时间点的中奖概率,用自己和亲属的账号抽奖;或是更直接地,篡改中奖用户名单。
诸如此类的细微调整,很难被监察者察觉,但总会留下痕迹。细心的监察人员们通过邮件、电话等渠道搜集举报线索,并主动对交易金额大、合作商多、掌握核心经营情况的部门数据,作专项梳理。
2018年,赵树远接到举报,称区域加盟商为偷逃运费,贿赂分拨中心物流人员,虚假降低货物重量。
根据线索,他和同事在系统中创建“风险模型”,获取几个字段数据:商户名称与编号、货物过磅时间、扫描货物的把枪编号、扫描人员工号,以及扫描后上报的货物重量,和分拨时系统自动称重重量。对比两个重量的差异,公司可以定位受贿员工,并集中获得问题商户名单,在月度结算时讨回运费差额。
这是最理想的反腐状态——帮助公司避免,或是追回损失。更多时候,贪腐行为完成后,监察人员才发现线索,再去处理,已经太迟。
更狡猾的舞弊者,修改上万条结算价格数据中的十几条,从中赚取差价。当财务人员发现该区域业务量越来越大,亏损也越来越大,赵树远和团队就出马了。他们四个人,拉出报价表格,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,浏览上万条数据,才找到那十几条异常,揪出贪腐者。
得益于技术,系统正变得更加智能。京东监察部总监段秋斌主编的《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》一书提到,2017年初,字节跳动开始建立专用数据库,花费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,监察、审计人员可以从中检索。此外,系统还会自动识别风险,推送给业务负责人。
每一天,大量数据被系统收集。这些数据成为资产。掌握了数据,就等于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和寻租的筹码。有人靠数据牟利,比如字节跳动两位前员工,离职后窃取公司源代码和技术资料,创立某短视频APP,并入侵公司服务器,获取用户信息,将内容用于该APP。两人因犯“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”,被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。
也有人靠数据窥探隐私:曾有出行平台客服在后台调取伴侣打车记录,判断其是否忠诚,后客服被移交公安处理。
任何权力都需要边界,包括数据的权力。自2015年起,《网络安全法》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、《数据安全法》等法律陆续实施。为了合规,也为了减少腐败,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使用方式定下严格规范:不同数据按照级别分类,授予不同权限的员工,数据导出需要逐级审批,明确使用目的、保留时间、销毁形式。
管理的“灰度”
但数据并不总是可靠。相信数据的互联网公司,也会被数据蒙蔽。
一个例子是,一家公司要在某城市投放共享单车,定下1万辆的KPI。城市管理要求规定,市区内只能投放5000辆,超过就要罚款。工作人员为完成目标,把多余的车放到偏远区域,根本没有人骑,无益于业务,但系统会显示,投放目标已经完成。
因此,监察不能只靠数据,还要借助制度与组织。十几年来,擅长迭代的互联网公司,逐渐迭代出一套完整的反腐体系。他们在业务部门内设置稽查岗位,在集团设立独立的监察部门,后者直接向核心高管汇报。查案之外,监察人员还要负责反腐宣导、流程完善,这在业内叫“事前,事中,事后”。
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六年前成立的阳光诚信联盟,由京东、腾讯、百度、美团等知名企业联合发起。该联盟已有近800家企业会员,他们组织同行交流与课程,上传、共享失信员工名单,拒绝录用失信人员。
“你不能保证公司的几万人都不犯错。监察体系存在的最大意义,在于让大家(对犯错)有敬畏心。”一位监察从业者说。
不过,在强调创新的互联网公司,普通员工对公司里的监察部门抱有过强的“敬畏心”算不上好事。另一个接受《财经十一人》采访的某平台监察人员告诉我们,他能感觉到业务部门的恐惧。他觉得如果业务部门主动与监察者交流,预先完善流程,一些舞弊事件本可以避免,但至少在他任职期间,公司业务部门很少有人这样做。他觉得,其他人无法向监察部门“敞开心扉”。
实现两者微妙的平衡,需要管理智慧。段秋斌主编的《互联网企业反腐密码》将其称作“管理的灰度”:“如果一个控制体系能够严丝合缝,把所有的潜在问题都处理掉,这个体系得多违背人性。……所有的创新活动,都会被严苛的制度盘查,让人激情耗尽。所以,有效的管理一定要留有行动空间。”
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面对这一矛盾,追求效率的互联网公司顾虑更多。在激烈竞争中,技术已不再是壁垒,为了快速占领市场,互联网公司大多采用扁平化组织架构,层级更少,指令才能更快贯彻。这也赋予业务一线的基层员工贪腐的权力。
“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寻租。扁平化组织必须充分授权,基层员工职权被放大,腐败的可能性就提高了。”段秋斌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。
用大闸蟹举例的施嘉,就处理过类似的案子。一位公司里职级最低的员工,负责外部车辆调度,靠收取司机的好处费,一年时间就赚到四万元,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。
而当公司壮大,业务与市场份额变得稳定,下放的权力、资源与贪腐的机会,又收拢回高层手中。与只能认罚的基层员工不同,高层有资源、有人脉,能够利用手中的筹码,和公司、 老板博弈,降低自己登上失信名单、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。
比如,在某头部互联网企业,一位业务负责人通过公司的对外投资拿“回扣”,被公司发现。长期多次协商后,他退了钱,主动离职,没有受到其他处罚。
另一些时候,腐败甚至成为老板默许的、实现公司业绩增长的工具。手机游戏行业高度依赖渠道,且手游“来钱快”,只要能上架、拿到渠道流量,就有收入。这里也是贪腐的重灾区。一位知情人士称,在手机游戏行业,渠道人员掌握上架游戏的权力,游戏公司会“收买”他们,确保上架并获得更高曝光度。而竞对公司会搜集证据举报,让渠道人员被开除,因为“收买”新人的成本,比“收买”已被竞对拉拢人员的成本,要低得多。
该人士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,一些游戏公司甚至会深入分析渠道方的员工守则,精准把控尺度,确保举报的结果只是开除,不至于移交法办。
按照刑法规定,非公受贿(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)、职务侵占(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便利,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)等行为,不论公司是否报案,只要公检机关发现,就能处理、起诉。但一般情况下,如果公司不报案,警察很难发现线索。
所以,现实便是如此——舞弊如何处理,反腐如何收场,全由老板定夺。将互联网员工贪腐金额形容为“可怕”的王宣,对此相当自觉:“我只是打工人,他们贪的不是我的钱,是公司的钱,当然要看公司怎么处理。”
“老板心里有一杆秤。”赵树远说。舞弊人员的岗位暂时无人能接替,上市公司公开贪腐高管案情会影响股价,招采流程违规的供应商是老板利益互换的对象,这些都是需要计量的价码。公司利益是永恒的秤砣,当秤砣下坠,老板的指令就从“一查到底”变成“先放一放”。
一位公司管理人员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,公司的薪酬体系相对固定,在业务快速发展时,会出现员工薪资和他经手的业务体量不匹配的情况,如果是相对隐蔽的行为,会考虑“先放一放”,但如果被查出来,肯定要处理,“否则会让其他员工以为公司是容忍贪腐的。”
在传统行业工作时,赵树远曾被卷入派系斗争,收到攻击竞对的线索,被“当枪使”。但他毫不在意。只要线索属实,他就去查,然后实时向老板汇报、沟通进展,“说到底,我们也是老板手上的一杆枪。”
所以,“向上管理”很重要。这让他了解公司的利益考量,避免做无用功。“不管干什么工作,都要把自己的定位拔高一点,”赵树远总结,“要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。”
一些监察人员据此总结了一套生存智慧:反贪不是“非黑即白”,唯有利益永恒。
人性的正反面
现实中,很多贪腐方式并不高明。比如某互联网公司,员工有加班后免费打车福利,一位员工与网约车司机约定,司机将员工送回家后,不结束订单,用另一部手机在其他平台接单,再将原订单费用分成。半年下来,该员工的打车报销费近20万元。这个在系统中如此显眼的“20万元”,让赵树远难以理解:“这不是个傻子吗?”
有“打工人”自觉的王宣,遇到的案件同样明显得离谱。他去前置仓检查,发现合同里写的150平米仓,连80平米都不到;仓库还被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转租给煎饼摊,搞二道经营,虚报的租金被负责人私吞。
在大厂工作的不安全感,或许是贪腐者的动机之一。一位前美团员工年纪渐长,担心自己会被裁员,不好找新工作,于是选择出售实习生名额,希望赚点钱,也积累点经验,以后转型做就业指导。这属于典型的非公受贿,他因此被美团开除。
商业媒体36氪则写过这样的案例:2014年前后,王宇(化名)在一家O2O公司做地推,后升为城市经理。通过抽成、虚报兼职人数等方式,他一个月能获得数万元灰色收入。
加入公司前两三个月,他经常倒贴钱跑业务。但他身边,越来越多同事收取上万元贿赂却安然无事;一个90后同事,工作一年就在二线城市市区全款买房。想到自己身在北京,每月只有几千元工资,他也屈服了,并心安理得:“公司一年融资上亿美金,一天花的补贴上千万,那么多钱撒出去就没影了,我多拿的这几万块钱只能算九牛一毛。”
在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创始人Jane F. Mutchler 提出的“舞弊三角理论”中,这种想法属于“自我合理化”,是企业舞弊行为发生的三要素之一。另外两个要素,则是“压力”和“机会”。
其中,“压力”是动机,大多指向经济。京东监察部总监段秋斌发现,以前员工贪腐,更多是因为家庭困难、经济拮据;而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住豪宅、开豪车、买名牌包,或是偿还赌债、游戏充值、甚至打赏心仪的网络主播而贪钱。
理论之外,面谈或许是监察者们了解王宇心理的唯一机会。正式的谈话,一般在掌握证据后进行,地点通常是会议室,现场录音、录像,至少两位监察人员在场。
要将达到犯罪门槛的员工移交法办,证据之外,本人口供也很重要,尤其对于非公受贿罪——贿赂隐秘、私下,只有得到本人承认,才能板上钉钉。因此,赵树远把谈话比作“射门”:一场足球赛,不进球,踢得再好,都是0分。
刚干监察的时候,他二十六岁,第一次找人谈话,不知道要问什么,“比对方还紧张”。没别的办法,只能边做边学。八年过去,他总结出一套技巧,把谈话分成高压突破、唤醒初心、权衡利弊、亲情感化四个环节,对应不同策略,有硬性的“讲政策、讲后果”,也有柔性的“换位思考”。过程中,还要观察对方的眼神和举止,比如“不假思索直接回答,值得怀疑”,“如果对方嘲讽问题,是不想让监察者再问下去”。
但这类方法论不是每次都奏效。面谈是对人性的检验,也因此变化多端。有伪造发票、虚假报销的员工,面谈中称自己身体不适,当场请假,请示上级,居然得到批准。半年后,批假的上级也被查出虚假报销,受到处罚。
还有收取好处费的基层员工,在面谈时情绪平静,认真听监察人员讲话,但就是不认罪。监察人员展示他人证词、转账记录,他还是不认,甚至当场把自己手机上的红包记录删除。虽没得到口头承认,但证据已经确凿,公司最后将他开除。
更多的人承认罪行,乞求公司原谅。有贪腐人员被送进监狱后,家人哭成一团,赶来求情,甚至下跪。前电商平台监察人员施嘉也会心软,但只能安慰自己:幸好发现得早,若是放任,之后的惩罚会更重。
他将监察工作视为“治病救人”。去年年底,他与索贿未果的员工面谈:如果我们有私心,就会等你收了钱,再抓现行;但我们没有这样做,你的未来还长,我们不想让你的人生留下污点。这个毕业刚两三年的年轻人哭着说“谢谢”。这让他找到工作的意义。
偶尔,医生也会“生病”。一位大厂员工,深夜加班后被监察人员约谈。狭窄、不透气的房间,加上晃眼的灯光和持续的诱导式提问,让他“昏昏沉沉”地回答了很多问题。最后,公司给他安上“泄露机密”的罪名,将他开除,并收回期权。他还会进入阳光诚信联盟的黑名单,后面再难找工作。
离开公司后,他才反应过来,自己被冤枉了。他找律师,起诉公司,终于洗清罪名,拿回期权。在他看来,这次误会的起因是,老板要求监察人员快速找到泄密者,监察人员为完成任务,将他推出去“背锅”。
赵树远也曾接到举报,线索视频里,被调查人正请调查人吃饭。后经查实,他的监察同事向涉事加盟商索贿私了。最后同事被辞退。
去年夏天,因为所在业务遭到裁撤,赵树远离开了互联网行业。他本有调岗的机会,也有其他互联网公司开出丰厚薪酬,他没有接受。
他喜欢互联网公司平等、友好的氛围,在这里,部门领导甚至会给手下写周报,“汇报”一周的工作。但这无法抵消互联网行业带来的不安全感。
他亲眼看到一些业务,在短短一两年间,从疯狂砸钱急转直下,遭到裁撤,然后一批人被迫离开:“搞不懂哪一天,整个业务就没了。”于是,他选择回到传统行业,相信实体经济不至于像互联网那样“说不干就不干了”。
在赵树远做监察的这八年间,互联网历经打车、共享单车、社区团购等几轮疯狂的烧钱大战,逐渐冷静下来。应该伸展的触角已经伸展,应该占据的地盘已经占据。当新的地盘出现,巨头还会展开竞争,数额惊人的财富会再次流向基层,而有钱的地方,就会有腐败。
腐败源于个人选择,是欲望与现实的错位,互联网行业财富惊人,员工待遇提高的同时,欲望也被放大。多数情况下,管理、技术和法律都只能在事后发挥作用,且难以杜绝。粗放式发展已经过去,降本增效、减少漏洞,都需要精细化管理。近两年,互联网大厂频繁进行组织架构调整,狠抓贪腐只是其中一环,更重要的问题是:擅长进攻的互联网大厂们,如何守好阵地。
标签: